11月22日晚上,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二十二讲在文南楼 216 会议室如期举行。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毛亮以“爱默生的《论美国学者》:文本与事件” 为题进行演讲。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模式,来自校内外约200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参与讨论。讲座由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陈湘静主持,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于雷担任与谈人。
讲座以《论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为中心,结合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教育经历、写作与哲学思想,以及当时美国社会的民主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对经典文本进行了创新解读和重新定位,点明爱默生在《论美国学者》中对智性自由、智性民主的推崇,同时也为读者如何解读文本、理解历史事件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范例。

1837年发表的《论美国学者》是爱默生成熟期之前的作品,也是他接受了浪漫主义唯心论之后初步完成的三部作品之一。另外两部分别是1836年出版的《论自然》(Nature)和1838年发表的《神学院讲演》(“Divinity School Address”)。三篇分别从哲学、文化、宗教三个方面对美国文明中的核心问题做出思考和反思。
《论美国学者》可以被视为爱默生初步运用浪漫主义唯心论逻辑的写作,1840年之后几年中分别出版的《散文一集》和《散文二集》(Essays, First and Second Series)则标志着爱默生文学和思想成熟期的开始。《论美国学者》被许多学者解读为论证美国文化独立性和美国文学特殊性的文本,甚至被认为是“美国文化的独立宣言”。毛亮教授对这种论断提出质疑,并将《论美国学者》重新定位为对新英格兰哲学、宗教、文化的现状及未来方向的检讨和思考,乃至对当时美国民主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反思与颠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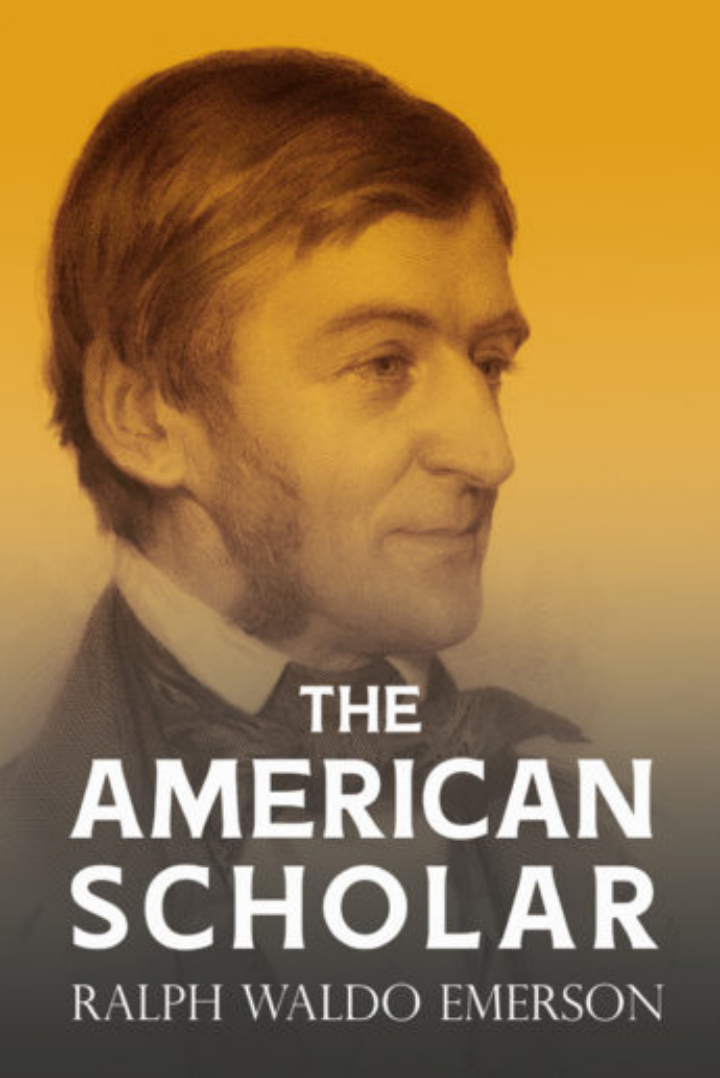
从教育经历看,爱默生在哈佛大学接受的是传统、保守的新英格兰绅士阶层教育。这种教育在哲学上表现为英国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和苏格兰常识哲学(philosophy of common sense);文学上呈现典型18世纪英国散文风格,讲求理性逻辑和文字文雅(propriety);宗教上以一元论(unitarianlism)为主,注重理性,强调正统的基督教义。爱默生的思想却与这种教育主张相背离,转向了浪漫主义和唯心论。毛亮教授特别提到圣经批评(higher criticism)对爱默生宗教观点的影响,促使他成为一个世俗化(secular)的学者。
讲座进一步指出,《论美国学者》的发表是美国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同时具有文本和事件两个层面的意义。毛亮教授引用了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论文《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中对“事件”(event)的论述,指出《论美国学者》的发表是一历史事件,它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想,标志着新的人性观、价值观进入美国文化。
当时美国社会流行的道德价值观是基于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对人性的理解(即“the mechanical scheme of empowerment and constraints”),认为人性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分别是经验主义的理性(reason),强烈的心理驱动力(passions)和审慎(prudence)。这种道德哲学强调对欲望的克制和引导,培养审慎的理性选择,达到内心力量的平衡与制衡(equilibrium and balance)。相应地,由绅士阶层领导的精英主义民主也强调秩序、约束、标准,反对平等的政治参与;文学上也相当保守,主张克制人性,教化、引导和约束一般民众。
《论美国学者》发表于1837年,此时的美国正经历经济危机和宪政危机,民主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受到冲击破产,各方矛盾无法调和,自由竞争理念和制衡机制失效。这也成为了《论美国学者》的写作背景,正如爱默生在文中写道,“Let me begin anew”,重新建立社会道德的底层原则。
爱默生使用了“整全人格”(whole-man)这一浪漫主义哲学概念,强调人性内在的统一(unity)和人性自身演变、成长的特性(progressiveness),与18世纪人性观(mechanical view)形成对立。《论美国学者》中提出的“Man Thinking”强调智性活动的过程,将其置于人性的核心位置,而非18世纪人性观强调的“审慎”(prudence)。至于如何培养完整的人性、实现智性自我的成长,爱默生提出了三个方面(nature,books,action),可分别解读为客体,传统,以及社会行动。客体的作用在于实现人的智性自觉,通过自然和其他客体,达成自我意识的发现(“know thyself”)。这种观点体现了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色彩。爱默生强调在智性的基础上,对待传统应该采取对抗的态度,而非一味地崇拜和尊重。爱默生还指出经验能够为自我意识、智性的成长提供资源,并通过社会行动成为思考的对象。这三者,即自我意识、文化传统和社会行动构成了新的有机体,颠覆了原本的政治道德基础(moral-political infrastructure)。这种对智性活动本身的依赖也体现在爱默生1841年发表的《论自助》(Self-Reliance)中,影响了爱默生对所处时代的乐观评价以及他的作品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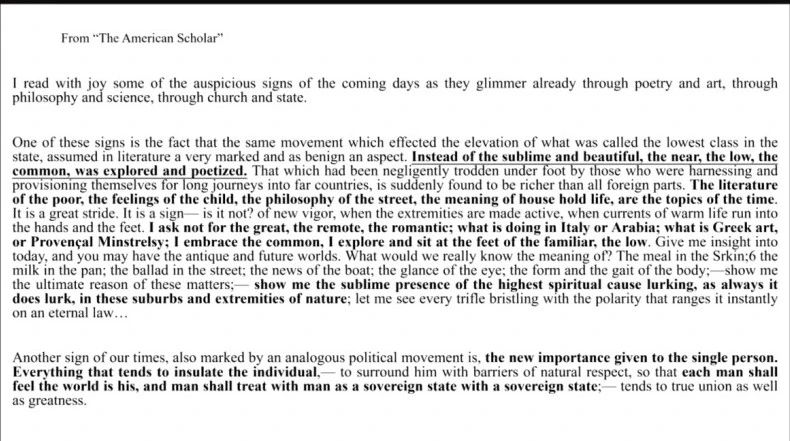
爱默生在《论美国学者》中展现出在智性自我的前提下,美国文化有可能形成的新观念和写作风格,一种新的修辞的可能。“Instead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the near, the low, the common, was explored and poetized...”当人有了智性自觉的能力,就能够把经验中的细节变成思考的对象;由此一来,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象征,正如文本中的“the milk in the pan”“the ballad in the street”。爱默生喜欢使用的“高低搭配”,例如“literature of the poor”“philosophy of the street”也体现了这一观点。这种思想也对文学创作的风格产生了影响,如惠特曼(Walt Whitman)和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诗歌创作。

讲座最后,毛亮教授对如何理解《论美国学者》进行了总结,指出不应从美国文化独立性或是美国文学特殊性的角度去阅读这篇文章,而应该考虑其对于价值论、人性论的颠覆性讨论。爱默生试图通过《论美国学者》在民主理念中建立一种新的、智性自由的维度,探讨将其作为民主基础的可能性。智性自由强调一种非功利的思维方式,尊重个体,认可智性活动的力量和人的内在不断成长的可能。这种理念连接了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创造性地指出了制度本身蕴含的一种可能性,即用智性民主来解决美国社会的各类问题。

在与谈环节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于雷教授就讲座的思辨性和深刻性进行了点评,并为《论美国学者》的文本解读提供了补充性的维度。于雷教授认为,毛亮教授不乏有趣地提及爱默生与爱伦·坡(尽管二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较为紧张)在质疑民族文学这个议题上所表现出的难得的默契。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在论述“爱默生美学”之际从爱默生的警句文体风格中所揭示的那种超民族性。于雷教授认为,这确实与爱伦·坡对民族文学的质疑存在相似之处。于雷教授还注意到文本中所流露出的“珍爱命运”(amor fati)之主题——这也正是尼采哲学中的要素:生命中的一切事物无论好坏都有其价值,并且可以成为智性成长的历程。此外,于雷教授还特别强调《论美国学者》中所主张的“创造性阅读”(creative reading);创造在爱默生那里不止于物的创造,更意味着思想的创造。这种对创造性的关注让我们想到了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所提出的“真理即创造物”(verum factum)理念,也即真理与创造物可以互相转换。这对于理解爱默生哲学思想中的宗教世俗化取向有一定的价值。最后,于雷教授引用了尼采对爱默生的评价作为结语:“爱默生有一种宽厚聪慧的快活性情,足以消解一切认真态度;他全然不知道自己已多么年老以及将多么年轻。”

文|杜宣熠
图 |毛亮 李佳静 杜宣熠 张晓婵
编辑|沙克尔江
审核|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