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月 11 日下午,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九讲在文南楼 204 会议室举行。中山大学英语系朱玉教授以“‘回忆往事如注视水下’——共读华兹华斯《序曲,或一位诗人心灵的成长》”为题进行演讲。
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线下结合模式,来自校内外 300 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参与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教授担任与谈人。讲座由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本次讲座从写作背景、作品主题、篇章结构、关键词语等多个维度对英国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的《序曲》进行解读,重点以“回忆往事”为切入口,在共读诗篇中带领听众领悟华兹华斯对心灵长河的自我探索。

朱玉教授首先对《序曲》的写作背景和全书结构进行了介绍。作品写于华兹华斯人生中的“奇迹之年”——1798 年,亦即英国浪漫主义奠基之作《抒情歌谣集》诞生之年。诗人与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相约前往德国,却因经济拮据等原因,被迫住在异乡偏远的地方,这使华兹华斯产生思乡情绪,开始追溯生命的源头。据朱玉老师介绍,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将《序曲》的结构大致分为两部分,前八卷构成一个乐章,讲述对大自然的爱如何引向对人类的爱;这与《丁登寺》所写的在自然中谛听人性悲曲、通过自然领悟人性的主题一致。后六卷由此转向人间,其中第九到十一卷描写寄居法国的经历,与诗人对法国大革命认知的转变紧密相合;第十二、十三两卷则反思人间经历如何削弱了审美和想象力;第十四卷对此做出回应——想象力如何得到修复。
值得注意的是,第六卷和第十四卷都出现了“攀登”片段。朱玉教授指出,两次“攀登”之间跨越的是人间的与心灵的低谷。《序曲》反映了一种迂回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是心灵的风暴,也是心灵成长的能源。在第十四卷攀登斯诺顿峰片段中,诗人仰望山巅的满月,见证“心灵的表征”;也俯瞰山谷云海的裂隙那“幽暗的渊洞”——与第六卷攀登阿尔卑斯山过程中所写的“狭长的地裂”、对立统一的山谷呼应。根据《序曲》译者丁宏为教授的解释,孵拥渊洞的含义虽复杂,但可简化为明月倾听喧声的姿势。明月静辉凌驾于万物之上,给混沌带来秩序,而最深处的黑暗、最底下的喧杂则代表着无序的神秘、潜在的能量、涌动的欲念等。云洞将上下连通,使明月与水声、上方与下界之间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虽是外在景象,却表现内在的关系与过程。华兹华斯在诗作中描写了很多壮美的自然景色,但他最终将笔锋聚焦到心灵成长,因为,无论人们出于希望或忧惧经历了多少革命式巨变,世事的体系终未改变,人类的心灵比其居住的大地美妙千百倍。

“回忆往事如注视水下”,这是本次讲座的标题,也是《序曲》第四卷中的诗句。诗人从剑桥回到了湖区,湖区承载了他童年时期的回忆,也是许多诗歌的来源。华兹华斯的许多诗歌并非即兴而发,而是在平静的回忆中沉淀写就的诗篇,符合他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对诗歌的定义。在唯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感性的回忆也是制衡抽象“理性演练”的方式。
但这种回忆并不等同于完全重现过去,它蕴含着再创造的力量,如同从船舷探身,俯视水面,水下的鱼儿和水草代表岁月本有的事物,但小船的摇晃和阳光的折射让人分不清影像与实体,则体现此刻的影响。华兹华斯俯视岁月的水面,“回忆往事,我常自觉有两种意识,意识到我自己, 意识到另一种生命”。朱玉教授介绍了华兹华斯重要的诗学概念“spots of time”(“瞬间”)。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些经历很平凡,但会突然产生深刻的含义。由于此类瞬间的意义主要是主观赋予的,因此证实了心灵的创造力。我们对这些瞬间的记忆对精神的健康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因为它们能在生命和想象的消沉时期帮我们滋补或修复心灵。华氏最伟大的一些作品应归功于这些瞬间,都讲述如何在平静中回忆它们(丁宏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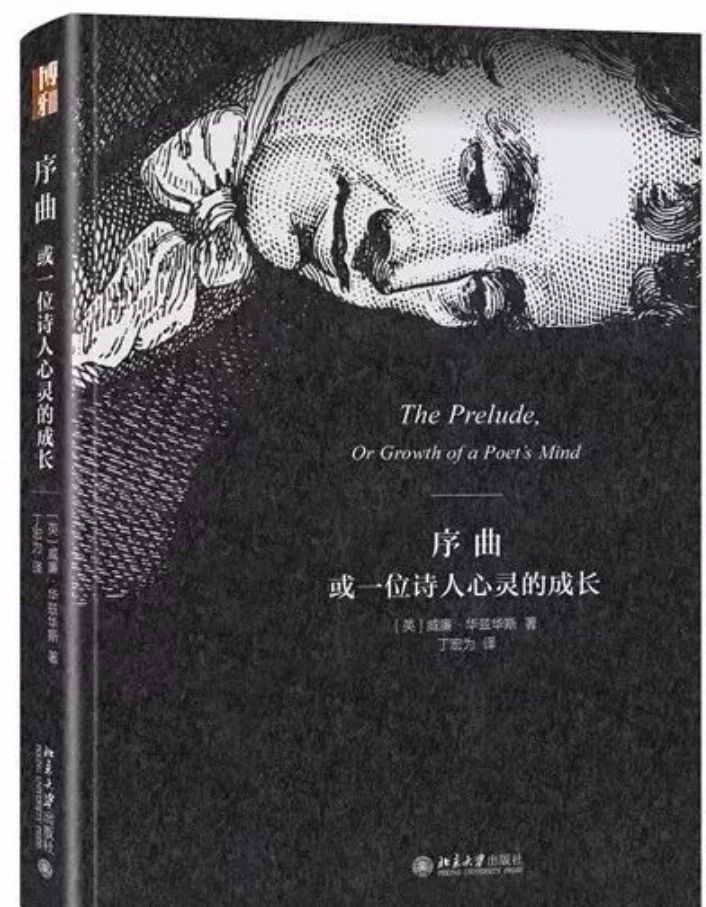
朱玉教授随后选读了前两卷中的“瞬间”,如偷船、滑冰等童年游戏, 这些具有相似结构的片段重点并不在于情节本身,而是超越眼前画面去感悟事件背后的情感与力量,华兹华斯认为“是情感的生发使事件变得重要,而非反之”。聚焦《序曲》第一卷滑冰片段,第一行“retire”一词的韵味十足,一方面它指诗中所写的离开喧嚣,从人群中抽离,另一方面也与诗人后来从激进的革命岁月中抽身、在独处静居中写诗有着遥远微妙的联系。《华兹华斯传》的作者Stephen Gill教授认为,诗人安家故乡湖区,不是退隐,而是找到了真正的战场所在。此外,这一片段也描写了旋转与静止,诗人顺应着地球的引力,但也具有跃出引力的力量——纵使周围事物继续飞旋,他也能站稳脚跟。

希尼(Seamus Heaney)在《华兹华斯的冰鞋》(Wordsworth’s Skates)短诗中描写了自己看到华兹华斯冰鞋时的反应。短诗传递着华兹华斯不拒重力且超脱重力的才能:他“沿着大地的弧线”写诗,将朴素的人和景物作为素材;但也与大地形成“切线”关系,以此“跃出大地的掌心”,体现超验的追求。朱玉教授特别解读了短诗最后一词“scored”,表面意思指冰刀在冰面上留下印记,也喻指着华兹华斯的诗作在大地和人心上留下烙印,具有恒久的感染力。
《序曲》第五卷的主题是书籍。诗人认为,书籍是一种略逊于大自然的教育手段。书主要指文学书籍,借指我们的想象力,保护书籍即保护想象和文学思维。诗人谈到当时压抑儿童天性的教育理论,该理论倡导儿童在成人的引领下成长。与之相对的是诗人笔下的温德米尔少年,夜晚时分独自一人与大自然交流。诗句中“hang” 一词尤其值得注意,该词在华诗中反复出现,可以理解为一种延缓、悬置(suspension)。诗中出现的“unaware”,“uncertain”等词或许和济慈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有某种相通之处,皆指一种向未知敞开的能力,即不急于确定事实,向神秘可疑的事物保持敞开接受的态度。
朱玉教授最后指出,虽然华兹华斯后期有转向守成的趋势,但诗人始终在进行一种创造性逆动,积极探索心灵之源。他深知悲曲是人生的基调,但总是通过回忆汲取力量, 收获“源自苦难的智慧”。与柯勒律治一样,他也认为灵魂自身必须散发出辉光,最终,若正确领悟生命的含义,“一切都表现欢乐”。

在与谈环节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老师阐释了对华兹华斯的新认识,并强调了华兹华斯的公众关怀,对朱玉老师的分享作出必要且有益的补充。他指出,朱老师的解读没有过多受文本历史背景的约束,透过历史细节看到背后的人性关怀。他认为华兹华斯描写心灵成长时,并没有让个人的感受过于膨胀而忽视了其他事物,而是将自然细腻地描写出来。诗人写自己在水上的倒影,也关注水下的景物,影子与景物交织穿插。华兹华斯的人文关怀恰恰是在对自然的描写回忆、对自己心灵深处的挖掘探索中显现的。陆建德老师特别指出,华兹华斯的社会社交生活也很丰富,具有公众的关怀,他的心灵成长不止生发于与自然的互动,许多成长来源于与同伴和朋友的交流以及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最后,陆建德老师还提到华兹华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启发作用。
文|李怡漩
图 | 道日娜 李佳静
编辑|沙克尔江
审核|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