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晚,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八讲在线上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陈永国主讲,以“《抄写员巴特比》:无望中的向死而生”为主题,深入探讨了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中的人性、语言符号、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等主题。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外文系副教授陈湘静担任与谈人。来自校内外百余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参与讨论。
讲座内容围绕《抄写员巴特比》的文本细读分析展开,在语言结构层面上探讨了意志与表象世界,象征性语言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抵抗关系,通过联系德勒兹“语言的牢笼”、弗洛伊德“死亡本能”等思想理论以及海明威、欧·亨利等文学家阐明了美国文学即将独立于英国文学之际所呈现的生命力、民主色彩与虚无底色。讲座语言富有诗意,信息充实丰富,为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读者提供了精彩的解读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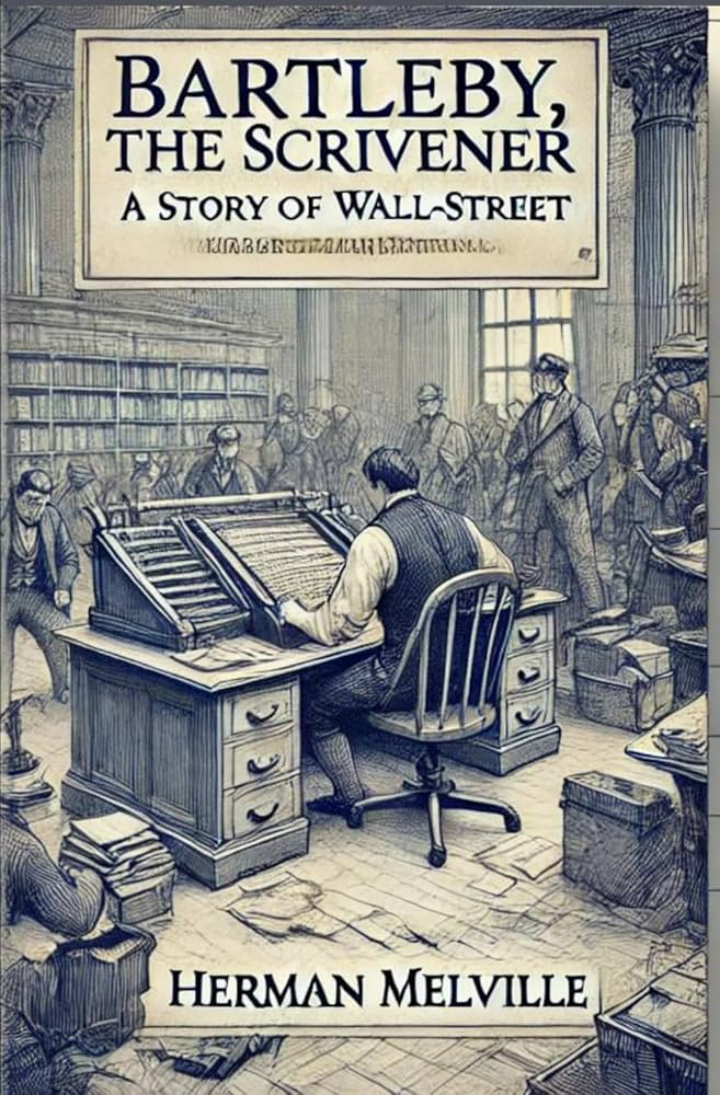
陈永国教授首先从标题“Bartleby, the Scrivener”入手,探讨了标题对大人物称谓的戏仿和修饰性称呼(decorative appell ation),以及如何通过语言中的转移,暗示巴特比有可能是金融大亨,让读者产生与故事相反的阅读期待。
接着,陈永国教授分析了小说中的环境设置。书中的“Wall Street”,并不是大名鼎鼎的华尔街,而是名正言顺的“墙街”。巴特比与毫无野心的律师老板一起生活在类似全景式监狱的条纹空间中,文中使用“Tame”一词,既诉说了客观意义的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也表明了主观意义的驯服、温顺、听使唤。陈永国教授认为,条纹空间的秩序感和窒息狭小,让巴特比失去了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从而完成了对人物的符号阉割(symbolic castration )。

陈永国教授演讲
从人物工作角度出发,陈永国教授探讨了巴特比身上无法逃离的“语言的牢笼”。巴特比的工作本是读死信,但他最终没有摆脱“语言的牢笼”,而是自愿沉沦,从一个条纹空间来到另一个条纹空间——抄写员。陈永国教授提出问题,为什么巴特比一直甘愿处于被阉割的状态?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语言符号与本我形象的关系,指出语言是缠绕在巴特比身上的一条“蛇”,即让他诞生了主体性,但是也让他丧失了主体性。
讲座的高潮部分是陈永国教授对巴特比三次拒绝老板请求的分析。陈永国教授草蛇灰线,回应了讲座开头埋下的伏笔——巴特比的“I would prefer not to”句式。“我宁愿不”本来应该是两者中更喜欢某物的选择,现在却变为了一个完全的否定。这种态度表达了身为弱者的本性,是死亡本能的一次显示;这种表达既是拒绝也是不拒绝,但却又很坚决。陈永国教授指出,领略他者意图,又表明自己立场,巴特比作为弱者只好用这种方式的重复来呈现自己的柔中有刚。老板貌似的热情让位给事实的无礼,老板的权力(power)让位给下位者(the powerless),这正是下位者向上位者发起的挑战,也是向死而生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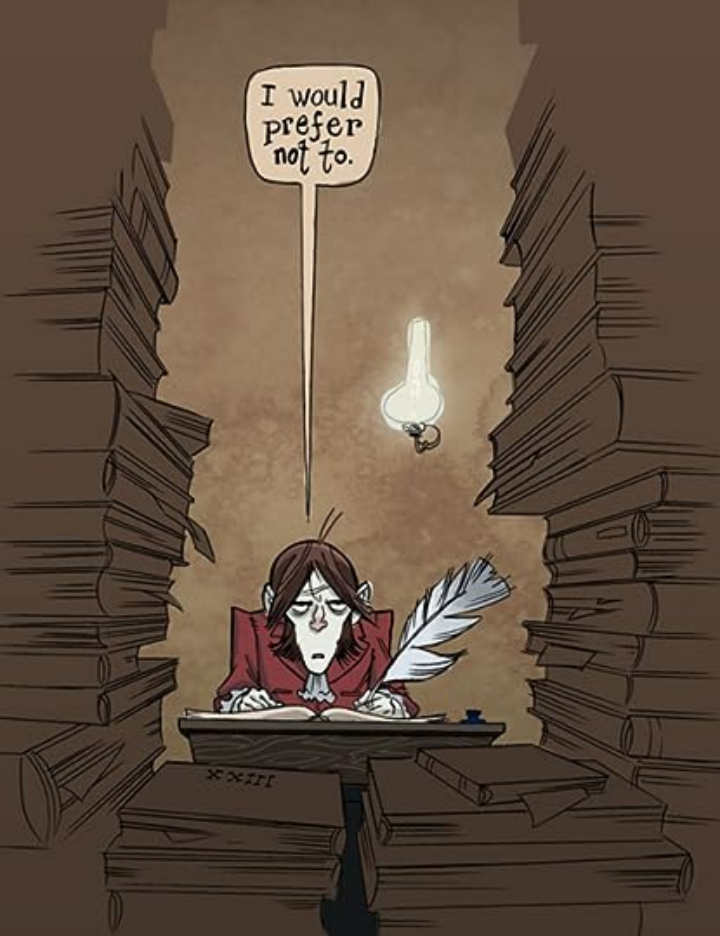
更进一步,陈永国教授从巴特比的行为中进一步提炼出了社会群体的普遍现象——人为了生存必须抵抗外部世界,也必须抵抗欲望无限碰撞的内部世界。对于这样永恒的矛盾,巴特比的处理方式是把自我(the ego of man)隐藏起来,像废墟里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无声沉默地伫立着,做一个固定的不想动的(A man without a place)并不特殊的人(A man without qualities)。他决定放弃符号阉割,但是他更加坚定地守在了条纹空间,孤独地面对着那堵墙掩藏的梦。
人所处职业的空间位置决定了人群的孤独,而巴特比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位置(I know where I am),也清醒地知道老板虚伪的面具下面同样孤独(I know you. I want nothing to say to you)。相比于不知身在何处的现代主义文学主人公,巴特比清醒而独立,绝不与整个社会同流合污,但是他的意志却被条纹空间所禁锢,被社会环境所制约,他自认自己并不特殊。只是,说自己不特殊的人,一定有他的特殊之处。
巴特比的力量也突破了故事情节,来到了语言结构层面。他以一个极为扁平的人物形象击碎了圆形人物的小说范式,但他也在语言的使用中生成了一个“新人”。陈永国教授指出,当意志与表象世界、象征性语言与社会现实的矛盾达到极限,两者便不再能够共存。最后语言的意志消亡了,但是语言仍然留存。“I would prefer not to”变成了单一的纯粹的否定,没有了想做的事情,只有对世界的否定,否定句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故事中的老板也开始使用,以至于这个句式被纳入了词典。
放眼小说诞生的时期,正处于美国文学即将独立于英国文学的十九世纪。故事里小人物对大人物说不,故事外黑人对白人说不,儿子对父亲说不。从意志(will)到强力(power),所抵抗的力越强大,生命力就也越强大。当时美国的社会环境正是孕育着如此向死而生的,积极的,但是不断被社会环境所否定的抵抗。但不幸的是,当最后抵抗的力量无法支撑原先的理想和状态时,就会走向消亡和虚无(nothingness of the will)。
对比《白鲸》中的亚哈与《抄写员巴特比》中的巴特比,前者是虚无意志趋势的偏执狂和恶魔,向自然不断发起超出能力范围的挑战;后者是天使般圣洁的疑病患者,选择意志而极端躺平,悬置过去与未来。但两者同样都是极端的神经症患者,他们的终极显示都是生命的死亡。

小说《白鲸》插图
陈永国教授最后总结,故事里的巴特比把语言沉默的力量推到了极限,这种沉默的力量打破了小人物忍辱负重的社会底层,也医治着病态的美国社会。但自由的制度化带来了无法逃逸的条纹空间,巴特比只能通过“解辖域化”从条纹空间来到自由身体自由发声的平滑空间,展开死信里带着生的使命奔向死亡的皱褶,将自我的异化和自我的攻击性联合起来,带着现代性的高傲逃离并摧毁现实世界。
在与谈环节中,清华大学外文系副教授陈湘静对陈永国教授的演讲作出了“有诗意、有个性、有深度”的极高评价。她梳理了演讲中对于弗洛伊德“死亡本能”、德勒兹生命政治理论和拉康“象征秩序”等理论的引用,并就律师和巴特比的关系作出回应。陈湘静教授认为,两者既可以解读成一种秩序及其抵抗的关系,指向社会批判,也可以着重分析老板的宽容和好奇,以此窥见美国民主的展望,即对“怪异性”(eccentricity)的包容。此外,陈湘静教授也提出疑问,作品中律师提到的上帝自上而下的宗教律令让他同情作为同胞的巴特比,而这样的观念是否与德勒兹的无政府主义民主主张有所冲突,两者又如何调和。

陈湘静副教授与谈
陈永国教授回应,这篇文本中并未明确表达宗教色彩,而是更多地从人的人性本身去讨论。老板的宽容与宗教中的兄弟情谊(fraternity)有所关联,但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巴特比怪异行为之下的无可奈何,更主要的是人的情感,是一种普遍的情感。主持人曹莉教授将巴特比的形象特点总结为被动的抵抗型(passive aggression),并指出麦尔维尔小说中“语言”主题的探讨空间。
在观众问答环节,同学还提及了性别研究和同性研究的文本分析角度,陈永国教授认为可以以此为角度寻找线索,但是主流研究认为重点并不在此。本次讲座为参与者提供了深入理解《抄写员巴特比》的机会,即使是线上形式,现场讨论气氛依旧热烈,研讨争鸣后,同学们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文|史芸千
图 | 张晓婵
编辑|沙克尔江
审核|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