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晚上,清华大学“英美文学经典的人文理解”系列讲座第六讲在杭州师范大学仓前校区恕苑19楼401教室举办。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殷企平以“《爱玛》中的反讽与幸福哲学”(Iron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appiness in Emma)为题进行演讲。本次讲座采取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来自国内外约300名师生聆听了讲座并参与讨论。讲座由清华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曹莉教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教授担任与谈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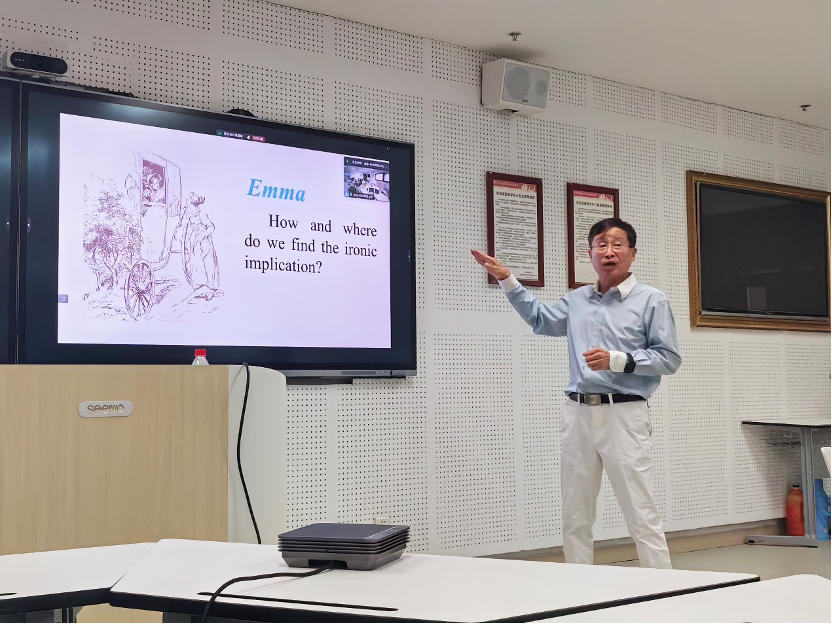
殷企平教授演讲
讲座从简·奥斯汀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回应出发,围绕反讽与幸福两个关键词,对《爱玛》这部小说进行了丰富细致的解读,同时也为读者如何阅读文本提供了生动的实践范例。反讽和幸福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何关系?殷企平教授开门见山提出,反讽实际上是奥斯汀在《爱玛》(Emma)中表达幸福观念的一种手段。
殷企平教授指出,简·奥斯汀在小说中对现代性这一概念进行了回应。现代性指的是一套关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这套价值观由启蒙思想家们提出,强调诸如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科学、技术、进步、民主、自由等关键词,其中核心之一就是幸福。奥斯汀对这套价值观的看法与启蒙思想家们不同,偏离了当时的主流话语。比如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莉迪亚想象着尘世幸福(earthly happiness)的可能性。有趣的是,我们也可以在启蒙思想家的话语中找到尘世幸福(earthly happiness)这个关键词。十八世纪,人们对幸福这一话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尘世幸福的确认实际上是启蒙运动的标志性胜利之一。简·奥斯汀在小说《爱玛》中提到,好人一起度过美好时光就是一种幸福,这与共同的快乐有关,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平衡,而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则强调工具理性。
殷企平教授认为,在简·奥斯汀之前,已经有大量关于幸福观念的论述,这些作品主要由哲学家、宗教作家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撰写。而一些非常重要的十八世纪小说家也对幸福这一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例如,《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中,男主角的父亲建议鲁滨逊留在“下层生活的上层”(upper station of low life),他认为这是“最适合人类幸福的”(the most suited to human happiness)。而在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小说《帕梅拉》(Pamela)、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的巨作《拉塞拉斯:一个阿比西尼亚王子的故事》(The History of Rasselas, Prince of Abissinia)中,也都提到了幸福的主题。殷企平教授指出,奥斯汀的小说表面上都有幸福的结局,但如果更深入地看每一部小说,仍会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
殷企平教授梳理了幸福概念的哲学背景。他指出,在简·奥斯汀出生前两年,劳伦斯·尼赫尔(Lawrence Nihell)就曾在书中对沙夫茨伯里(Anthony Ashley Cooper, the Third Earl of Shaftesbury)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思想进行了区分。前者认为人类是半神种族,后者则认为人类是一群魔鬼。两位哲学家理解人类的方式表明了他们对幸福的态度。霍布斯暗示幸福只能以某种自利的方式实现,而非经由人们共同努力。简·奥斯汀则通过小说参与了这场辩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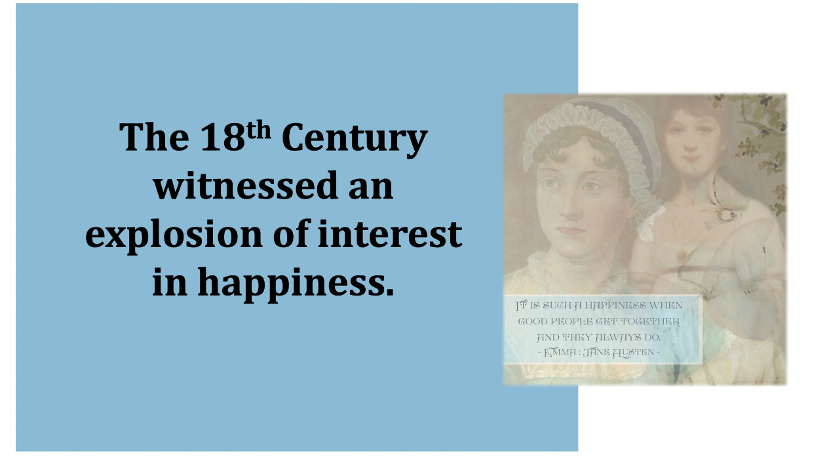
殷企平教授认为,简·奥斯汀对浪漫幸福并非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他指出,在《爱玛》中,简·奥斯汀将反讽基调贯穿整部小说来呈现幸福的概念。反讽(Irony)作为一种文学手法,通常分为三类,言语反讽(The Verbal Irony)、戏剧反讽(The Dramatic Irony)和情景反讽(The Situational Irony)。言语反讽是指说话者的意思与实际所说的正好相反。戏剧反讽意味着人物对现实的理解与现实本身存在差异。情景反讽则指向角色意图和事件结果之间的差距。那么《爱玛》中的反讽暗示在哪里呢?殷企平教授指出,《爱玛》中的反讽或反讽寓意经常被隐藏在作者如天鹅绒手套般优雅的写作风格之下,目的是遮盖作者的真实意图。
接下来,殷企平教授聚焦于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对文本进行了细致独到的解读。殷教授指出,文本细读的目的在于找出字里行间的讽刺、歧义、悖论、张力和多重含义。小说的开篇段落提到女主人公“俊俏”(handsome)、“聪明”(clever)、“家道殷实”(rich)、“性格又开朗”(happy disposition), 这些描述反讽意味十足。比如, “handsome”一词一方面说明爱玛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另一方面则微妙地暗示了男性的权力意志。殷企平提醒同学们,奥斯汀安排单词和短语的方式甚至顺序都十分重要,改变语词顺序意味着失去优雅和美感,小说行文的重音、音韵、语序等都经过了作者仔细的权衡和考量。最后,殷企平教授得出结论,奥斯汀对幸福的看法在《爱玛》中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其中反讽的语气巧妙地为女主人公的跌落埋下了伏笔,这也引出了整个故事的寓意:一个人必须谦卑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

讲座现场
与谈环节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陆建德教授就爱玛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点评。陆建德认为,爱玛的幸福观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构成因素,即履行道德责任、体贴他人。比如爱玛在对待自己的父亲时,展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宽容、善良以及自我克制,这在中国语境中会被称赞为孝顺,因此爱玛与父亲的相处片段在论文写作中或为不可忽视的一点。殷企平教授认为,爱玛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她的个性在故事发展中经历了转变。她确实很有幽默感,天生友善,经常愿意帮助别人,很热心。她的动机其实很复杂:一方面,她渴望帮助别人,另一方面,她又过分热情和傲慢。这是因为她看似幸福的处境一开始往往会滋生傲慢。但她本质善良,因此后来能够改变自己。殷企平教授还提出了故事的另一个维度,即失误,并指出简·奥斯汀与乔治·艾略特这两位女小说家所创作的两位女性角色的相似之处。陆建德还指出小说中另一人物泰勒小姐的重要性。泰勒小姐塑造了爱玛的道德品格,她是爱玛人格发展过程中的一位重要导师。爱玛在与泰勒小姐长达十六年的相处过程中变得聪明过人,还习得了令人钦佩的谈话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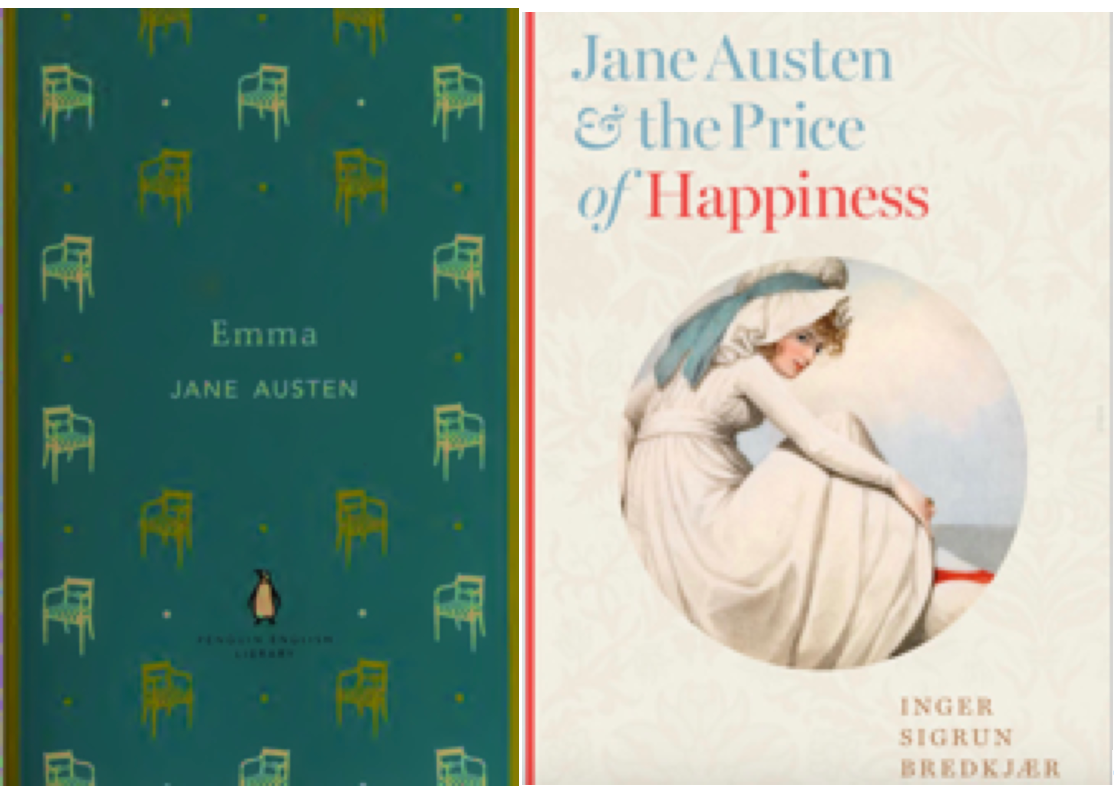
讨论环节中,曹莉教授指出,《爱玛》、《傲慢与偏见》等奥斯汀的大部分小说或可归为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或成长叙事(initiation narrative),主人公经由失误或过失实现自我的转变,从而更加了解自己和他人;以家庭和婚姻为题材的小说,看上去似与宏大的社会历史画卷无关,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最能映射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关系和矛盾冲突;奥斯汀对幸福概念和工具理性的态度和看法与启蒙思想家们的不同之处值得进一步探讨。线上线下的同学围绕奥斯汀小说中幸福与济慈诗歌中痛人的愉悦(aching pleasure)之关联、幸福与情动(Affect)之间的区别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讲座的最后,主持人曹莉代表线下线上的全体听众感谢殷企平的精彩演讲和陆建德的深入与谈。本次讲座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耿靖文
编辑|沙克尔江
审核|高阳